
看《风起洛阳》,咱聊聊马伯庸


时下,有部网剧《风起洛阳》正在爱奇艺热播,因听身边的朋友多次谈论它,于是,特意买了爱奇艺的会员,开始追剧。
必须要说明的是,我可不是冲着什么黄轩、王一博、宋茜、宋轶来追这部剧的,我是冲着马伯庸来的。
一口气看了四集,印象是:可看。但既没有像一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像一些人说的那么差。打7分,当属比较公允。
但是有一点,让我感觉有些奇怪,不是说这剧是根据马伯庸的小说《洛阳》改编的吗?但我在全网搜了一个多小时,竟没有搜到这部小说?昨天,才听一位同事说,这书压根儿就没出。那怎么叫根据某某小说改编的呢?可也没见马伯庸出来辟谣,说明他确实写了这样一部小说,只是如此改编,在我的记忆当中,古今中外,未之有也。
马伯庸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我看过他的《风起陇西》《古董局中局》和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
读马伯庸的小说,我常常会感慨,一个人的知识点,怎么会有这么多?这人以前得是一个多大学霸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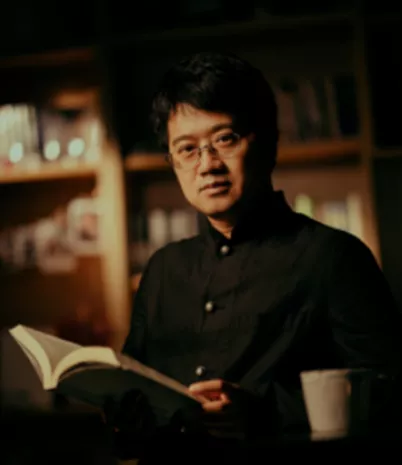
可看他的履历,也很一般:1980年出生在内蒙古赤峰市,成长于桂林。虽然他的父母都是高级工程师,但他从上中学以后,数学考试就从没及过格。他大学读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商学院,本科毕业后,又去了新西兰留了几年学。回国后,先是进了一家外企工作,他们那家公司叫施耐德电气公司,他尝戏言,之所以会选去这家公司上班,是因为有一瞬间他想到,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不会是施耐庵吧。
说到写小说,他说是从上大学时开始的。那时候(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们学校附近有个网吧,但20块钱一小时的上网费,对于他这个“穷学生”来说,实在是太贵了。为了去上网,他只能省下一周的早饭钱,周末跑去那里上一个小时的网。“我一直很爱看小说,但因为贵,所以不舍得在网上看,我就带了一个3.5英寸的软盘,把想看的小说拷下来,再到学校一块钱一小时的单机机房,把它读完。有一回,我的软盘坏了,小说的后半部显示不出来了。百无聊赖之中,就接着往下写了几十行,只当是打发无聊的时间了,等到了周末,我又去网吧,重新拷回了那部小说,竟发现我写的和作者写的,竟然是大同小异。原来我也能写啊!我想。”
以后,他就写起了小说。“大约是从1999年开始,我是写完一篇,就发到论坛里一篇,一开始,是在一个只有二三十人的小论坛里写,后来,看到反响还不错,就又到了一个大的文学论坛里写。我很喜欢当时的那种状态。我闷头写,大家闷头看,不知不觉,我和论坛里的很多人都成为了朋友。不过,那个时候,我还真没想过我以后要指这个吃饭,甚至连出版都没想过,就是觉得好玩,我把文章发上去,有人过来给点个赞、评论几句,就是最高奖赏了。”
但是随着给他的作品点赞、评论的人越来越多,他的“雄心”也越来越大。上班以后,在班上也经常会偷偷打开笔记本电脑,写上一会儿小说。当然“必须不能让老板发现,否则就会挨批评,甚至一月的奖金泡汤。”
马伯庸的作品大都充满了奇思妙想,亦庄亦谐,很快就拥有了一大批拥趸,并开始被各大论坛,以及平面媒体转载,出版商也找上门来……

他的早期作品《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就是他在重庆当销售时写的;《笔冢随录》则是他在北京亦庄的工厂里,伴着乏味的《技术手册》和热火朝天的生产线写的;公司搬到望京后,他又猫在一个别人看不到他在干吗的工位上,敲完了《破案:孔雀东南飞》。他以为公司的人都不知道他在写小说,但其实几乎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他在写小说,直到有同事拿着自己买来的他的书,跑过来找他求签名时,他才知道,原来自己这保密工作,做得也太差了。
2010年,他的《风雨〈洛神赋〉》与贾平凹的《一块土地》一起摘得当年的“茅台杯”人民文学奖散文奖;2012年,他的《宛城惊变》和《破案:孔雀东南飞》又获得了朱自清散文奖。
马伯庸红了,网友们还给他起了个外号——文学鬼才。因为你从他的文字中,总能感到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而且特别喜欢那些一般人觉得没用的冷知识,热衷于探究那些他自己觉得好玩儿的东西背后的故事,还喜欢把看似不相干的人、事、物以脑洞大开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然后用风趣幽默的语言,讲给别人听。
到2015年时,他已出了13本书。这得感谢他所在的那家公司的文化,不是那么“狼性”。
这时,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辞职。以后就一门心思写他的小说。“我都‘文学鬼才’了,还上的哪门子班啊。”促成他下决心辞职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他被检查出了疑似肺癌,当然是虚惊一场。当时,他正写着《风起陇西》,在等待确诊的日子里,他去重走了一遍诸葛亮的北伐之路,他说当他站在定军山上,俯瞰勉县时,立刻就明白了诸葛亮死后,为什么一定要人把他葬在定军山的用意。不过他说,这跟他的辞职没有关系,但我却觉得关系很大。
可是,当他辞职以后,却马上又遇到了一个麻烦——灵感不见了。
用他的话讲,就是“你不拿它当正经事干的时候,特别喜欢,一旦变成正了经事,感觉就不对了。”一度,他为了能够找回灵感,特意去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每天早上起来,先点上一根线香,再泡上一壶热茶,然后颇有仪式感地打开电脑,“一待一天,什么也没有写出来。”“灵感就像欠了你钱的朋友,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逮到他。”
好在这个时间不长,不久以后,他就又下笔如有神助了。
很多人对马伯庸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玩心很重的人,喜欢收集各种诡异的事情,发掘历史故事里的“萌点”,点评电影、网剧,追日漫,调侃同行好友,晒娃自黑……
“因为闲的。”马伯庸并不承认这是他刻意地在为创作找素材,纯属个人兴趣。“辞职后,我过起了‘放任自流’的生活。一般是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八点半出门,在家附近找一家咖啡店,然后在那里写上一天,我必须要在一个比较嘈杂的地方,才能写出东西,每天就像上班一样,要么去咖啡馆,要么去朋友的公司找个工位,因为我原来就是在工位上写东西的。有次我去天津,还在火车站的候车室,打开电脑写了半小时,感觉特别好。我写作的速度并不是很快,通常每天只写4000字,任务就算完成了。”
不过在成为职业作家以后,马伯庸对写作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写作这个事吧,是个70分靠技巧、30分靠天分的事。如果你只有技巧,能达到70分,写出来的东西不难看。你要再往上去,让你的作品成为经典,那就得靠30分的天分了。但是你就是再天才,也得老老实实地写,也得坚持。当年,我在论坛里写时,很多人比我有天分,他们随便写几句话上来,就特别惊艳。那会儿,我们都在上大学,后来找工作、找媳妇、生孩子,写作又没有给你一个合适的回报,很多人慢慢就把这事给搁置了,去忙自己的人生了。等到现在回过头来再想写,已经写不出来了。我从1999年开始写作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这中间就从没有间断过。至少和那些有天分的人比起来,我算是比较勤奋的吧。”
作家,与其说是一个职业,不如说是一种状态。马伯庸一直不认为作家有专业和业余之分,“我就是一个‘野生生长’的作家,我觉得这样挺好。”
马伯庸的小说基本上都可以归为历史小说,又或者说是“历史可能性小说”。什么叫“历史可能性小说”?
这词是马伯庸自己创造的。他也有解释过:“我一直很喜欢历史,但如果你去读史书就会发现,它的记载永远是片段式的,某人在某地做了某事。不仅时间不连贯,细节也不完备,这就给后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若是你能用你的笔,去将这些空间填满,就相当于是对历史做了一个修补工作,岂不是很有意义?
“记得我在新西兰求学时,有一年放暑假,我回到广州,那时候我还没有写过长篇小说,当时,我的床头放着一本陈寿的《三国志》和福赛斯的几本小说。我在百无聊赖中,几本书轮换着看。一天,我看着看着,有点困了,就在我迷迷糊糊的当儿,这些书好像突然交叠在了一起,我的脑子打了个激灵——如果我能把陈寿和福赛斯合二为一,按照冷战间谍小说的风格,写一个三国故事会怎么样?然后,我就简单地构思了一个故事,试着写了几段,发现很酷,就兴高采烈地写了下去。前几章一气呵成,写得我是茶饭不思。那种疯狂而又愉悦的体验,让我记忆犹新。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发现在历史的缝隙中,有很多可能性,可以挖掘。另外,我个人觉得,历史上的每件事都有一个内幕。如果没有,那就制造一个出来。对写小说来说,历史的真实性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要有意思。当然,我的这些猜想,未必是真的,我称它为‘历史可能性写作’,即在不改变历史的前提下,以全新的现代视角去诠释历史,在既定的历史里翻出新的花样,这就像是戴着镣铐跳舞,而且是戴着老式的镣铐跳现代舞。我想我会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下去,把‘历史可能性小说’的这个概念发扬光大。因为它太能满足我的历史情怀了。
“曾经也有人问过我,在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应该如何把握发挥想象与尊重历史真实的关系,对此,我赞成大仲马的说法:‘历史只是墙上的一个挂衣钉,而我写的小说就像是一件大衣,历史这个挂衣钉,就是用来挂我小说大衣用的。’但有两个原则,你不能违反:一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你不能随意去改变;二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性格和追求你不能随意去改变。只要守住这两点,其他的,你都可以尽情地去想象。”

的确,马伯庸写的是小说,不是论文,我想作为读者也能分得清楚什么是小说、什么是历史教科书。不会有人把文艺作品当真,只会说这个小说看起来很像是真的。而且他写的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应该算是历史传奇、历史猜想吧。研究历史,当然要严谨,但进行文学创作,就不妨大胆一点。让想象力飞起来,没什么不好。历史上的很多大事,隐藏在它背后的真正动机,都没有被史书记录下来,这就给了小说家一个腾挪的空间,你写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这是胡说,但同样看得津津有味。文学创作只要把握好“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这个度就行了。
而对于喜欢读史的人,马伯庸也给出这样一条建议:“其实,每一部历史小说都有它的现实意义,骨子里讲的都是当代史。如果一本历史小说,不能让当代人从中得到一些共鸣的话,那它就失败了。所谓‘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我始终认为,每个人读史都是有其目的,这很正常。但历史资料太多了,一般人很难知道从哪里入手。我教大家一个读史的方法,这方法不是我发明的,而是苏轼发明的,叫‘八面受敌读书法’,就是先选定一个方向,这时,你会有一大堆问题想要去解决,然后,你就专注于和这些问题有关的资料,一本书接一本书地去读,读完你会发现,很多过去你想不明白的问题,都已想通了,迎刃而解了。读史的魅力,我想也就在于此吧……”
最后,再说个跟马伯庸有关的有意思的事。一次,有位读者问他:“如果你能穿越回过去,你希望穿越到什么时候?”他说:“15年前,我想多买几套房。我可不想穿越回古代,因为古代没有抽水马桶。且很多我敬仰的历史人物,最后的结局都很惨。再有就是语言文字不通,听不懂人家说啥,也不会用毛笔写字,写古文也没法跟古人比,而且谁能保证穿越到古代,自己对古代的病菌有没有抵抗力,活不活得下来,都成问题。我是个特别惜命的人,求生欲很强。总之写小说可以天马行空,真要穿越回去,就不得不考虑这些现实的问题。我现在喜欢在全国各地溜达,因为有车、有高速公路、有手机、有钱,这要搁古代,出门就不安全了。”
作者:木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