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文斌是同仁医院眼科专家,从医院官网翻看他的简介,你会发现肿瘤两个字出现频繁。是的,他就是国内第一位通过局部切除的方法,治疗眼部脉络膜黑色素瘤的医生,终结了我国眼癌患者一旦得了这个病就必须摘掉眼球的历史。

一大早,魏医生的诊室里就站满了患者。他们当中绝大部分病人是从外地专程来北京找魏医生的。“你去北京吧,找北京同仁医院的魏文斌大夫,这个病只有他能治。”一位患者的妈妈说,当地医生跟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她蹲在地上哭了很久。

魏文斌是同仁医院眼科专家,从医院官网翻看他的简介,你会发现肿瘤两个字出现频繁。是的,他就是国内第一位通过局部切除的方法,治疗眼部脉络膜黑色素瘤的医生,终结了我国眼癌患者一旦得了这个病就必须摘掉眼球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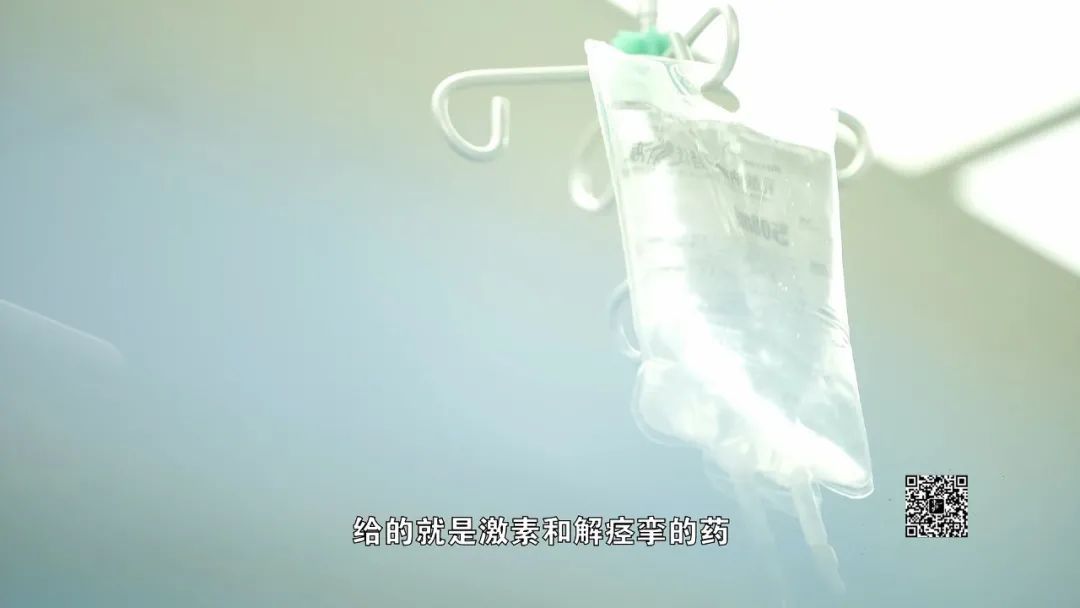
诊室内,一个内蒙来的姑娘安静地坐在医生面前,要不是在这里遇到,很难相信那双大眼睛里埋了那么大一个“定时炸弹”。一旁的妈妈双手合十,不时地擦拭眼泪。“你这个没事,不要紧张,交给我,放松心态,好好配合。”听魏医生这么说,姑娘笑了。姑娘是当地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她很漂亮,但我不敢看她的眼睛。

一位东北口音的女子,40多岁,身穿一件修身皮衣,麻花辫上戴着一朵紫色的花,一个精致漂亮的女人,然而整个问诊中,她攥紧的拳头始终没有松开。“你这个肿瘤有点大了,建议做眼摘,这样更保险,之后可以安个义眼,不影响美观。”听到魏医生的诊断,她握紧的拳头从两侧抬起放到了腿上。那一刻,很沉重。

眼睛里面有两大恶性肿瘤,一个是小孩得的,叫视网膜母细胞瘤,有化疗等一些治疗方式,并不是全然没有对策;成年人得的就是脉络膜恶性黑色素瘤,恶性度高,有相当一部分就转移了,而且多半会转移到肝脏。以前得了这个病,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把眼球摘了。

“说实在的,眼科大夫是很愿意做手术的,白内障做一个复明一个,多开心,视网膜脱离做完了,网膜复位了,视力恢复了,是外科大夫愿意干的事。但是黑色素瘤来了就得做眼摘,我们眼科医生心里那一个疼,因为你没有办法。眼科大夫最不愿干的事情就是眼球摘除,”魏医生说。

其实我们都知道,如今手术切除是治疗癌症患者,尤其是早期癌症患者的有效方式,那眼睛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这个手术太难了。

我们的眼睛特别娇嫩,除了神经组织,还有很多血管组织,一碰就容易出血,在直径23毫米的眼睛内,不但要精准地把肿瘤取出来,还得让眼球其它地方都不能有问题,这就很难了。再加上脉络膜是个血管膜,一切它可能就会出血,皮肤上出点血没事,但眼睛里面出血,患者就看不见了。然而,这样一个看似不可逾越的难题,魏文斌找到了解法。即使现在,国内外真正能做这个手术的人依然非常有限。

临近6点,病人渐渐离去,喧闹了一天的诊室安静空荡。在魏医生的诊室里,我们对面而坐,开始了正式的采访。这位国内眼底病首屈一指的大专家谦逊和善,言语中略带一点南方口音,虽然刚结束一天的工作,仍然很热情认真地接受采访,看不出倦怠。他从1986年7月13号开始讲起,那天,一个风尘仆仆的医学生,坐着火车一路咣咣铛铛地从安徽来到北京,来到同仁,一晃30多年。

那晚听魏医生讲述曾经手术台上的那些紧迫与不甘、患者突然离去的痛惜和无措、广袤草原上的纠结与孤单、还有夜深人静时细细品味过的兴奋与谜团,我突然明白了,他之所以能屡破难关,实现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不但源于他在工作中超乎常人的坚持和努力,更源于他对医者的责任和仁心的深刻理解。“医生在很多的时候,就是要有一点冒险的精神,把一些不确定的东西变成确定性,把一定的风险给它化解,确实是需要医生自己的一种担当,也需要病人的理解,”魏文斌说。

冬天天黑得早,不知什么时候窗外的霓虹灯渐次亮起,采访结束,临走送我们出门时,魏医生在白大褂外面套了一件黑色羽绒坎肩儿,随口说了一句“年纪大了,容易感冒。”希望魏医生保重身体,为更多处于绝望的患者带来希望,留住光明。
编导 : 张晓沁
编辑 : 栾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