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着一支老式的“派克”钢笔,暗红色的塑料质笔身镀有金色的圈纹,已经有些变黑的金黄色笔头上依稀可以看出“PARKERJUOFOLDPEN”字样。这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8年送给当时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钢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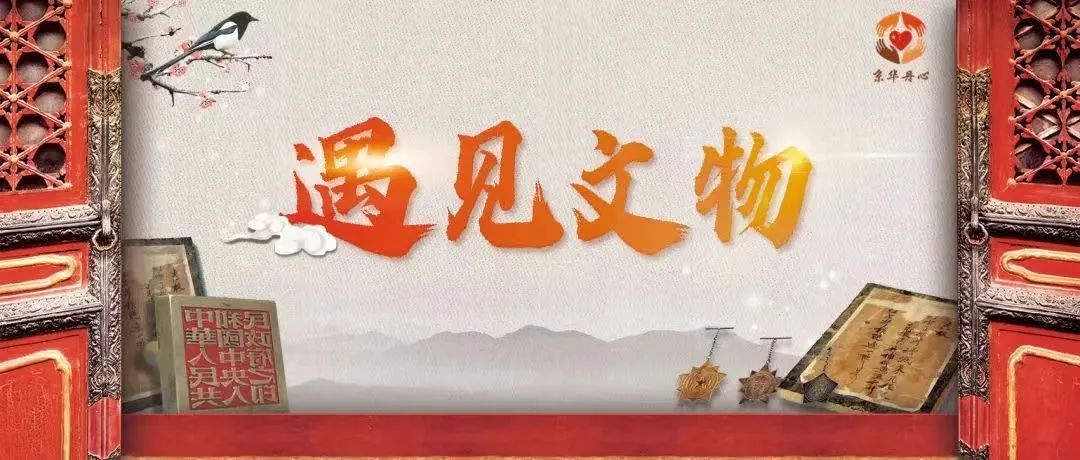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着一支老式的“派克”钢笔,暗红色的塑料质笔身镀有金色的圈纹,已经有些变黑的金黄色笔头上依稀可以看出“PARKERJUOFOLDPEN”字样。这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8年送给当时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钢笔。
文物展示

斯诺赠送项英的“派克”钢笔
埃德加·斯诺,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1928年来华,1936年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将他在延安的采访记录整理成集,取名为《红星照耀中国》(中译名),于1937年10月在英国公开出版,一时轰动了世界。
1938年7月,斯诺从香港抵达武汉。8月,他会见了新四军军长叶挺。后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采访了新四军政委、副军长项英。

1938年,周恩来、邓颖超和斯诺在武汉
项英是我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10月,项英领导机器厂工人罢工,取得胜利。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项英到上海、汉口,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31年,项英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临危受命,担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率部策应红军主力突围转移。项英送走中央机关的最后一支队伍后,面对的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局面。斯诺曾在《项英的一支铁军》中写道:“只有3000个正规红军留了下来,其他另有7000个赤卫队,2万个党员的非正规军(游击队)。他们所有的武器是一万支来复枪、几十挺机关枪、几门陈旧的迫击炮以及旧式的兵器,其他的只以手榴弹、刺刀、大刀、长枪作武器。”
1935年5月,国民党大军约50倍于游击队的兵力对赣粤边游击区进行全面“清剿”,叫嚣要在3个月内“打死、饿死、困死”游击队员。由于敌人的封锁,红军游击队的生活极为艰难,他们夜里不敢在镇上或村里睡觉,怕遭敌人的突然袭击,只能在山林里风餐露宿。可即使如此困难,项英还是抱着必胜的信念,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在群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进行了长达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项英、陈毅等的指挥下,红军游击队机动灵活地在国民党军队四面夹击中求得生存。1934年秋至1937年夏,南方8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仅保存有1万多人的力量。但是,这支人员不多、装备简陋的队伍,却是经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浴血坚持保存下来的精华。他们很快奔赴抗日前线,驰骋江淮大地,成为了让日寇闻风丧胆的铁军。
在1938年的这次采访中,项英向斯诺谈了自己的身世和革命经历,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之后,他和陈毅等一起领导部队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怎样以斗争求生存,并和大于自己数十倍的敌人周旋等等的经历。

1938年1月,南方游击区领导人在南昌的合影,前排左四为项英
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和新四军抗击日寇的事迹让斯诺对项英由衷地敬佩。斯诺曾感叹说,“项英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他更加坚定地认为,红军和游击队这样一支“决死”的部队,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采访之后,为表示自己的敬佩之情,斯诺把自己从香港带来的一支“派克”钢笔送给了项英。对于作家和记者的斯诺来说,没有比笔更好的礼物了。
斯诺把对项英的敬意化作笔下的激情,很快写出新闻通讯稿向全世界发布。1939年,斯诺采写的长篇通讯《项英的一支铁军》在美国《亚细亚》月刊当年5月号发表后,被上海的《良友》画报和《华美》周报翻译转载。后来,斯诺又采写了很多有关新四军的报道和通讯,让不少海外人士对新四军在江南坚持抗日斗争及其发展壮大,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
项英也非常珍惜这支钢笔,一直随身携带。他用这支笔,不知草拟了多少文件,写了多少篇重要文章。如《新四军一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论目前国内外情势》《本军成立两周年纪念感言》等,都是这期间的重要著作。
1941年1月,蒋介石调集兵力,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伏击了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虽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遭受重大损失。3月14日凌晨,项英率周子昆等隐蔽在赤坑山蜜蜂洞,准备待机北渡,不幸被叛徒杀害。
项英牺牲后,他的警卫员携带这支钢笔,历经艰辛,突出了敌人的重围,将它交给了新组建的新四军第7师政委曾希圣,曾希圣把这支笔交给新四军军部的通信科长胡立教保存。1943年,胡立教又把这支笔交给了军部的机要秘书顾雪卿。新中国成立后,顾雪卿把珍藏多年的这支钢笔送交到南京军区干部部。1959年,南京军区又把这支钢笔送给军事博物馆珍藏。
来源:“军博红色少年”微信公众号


